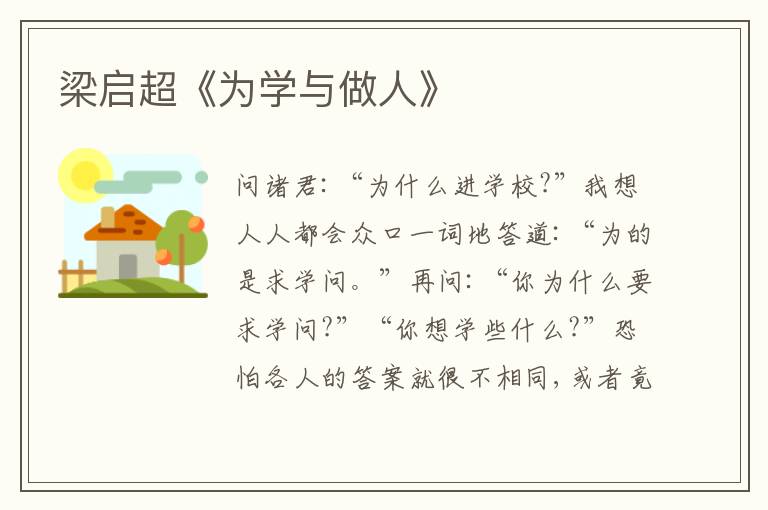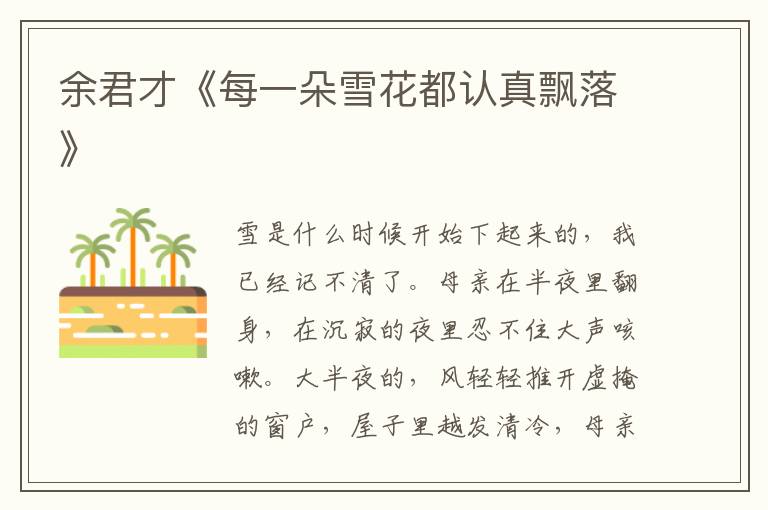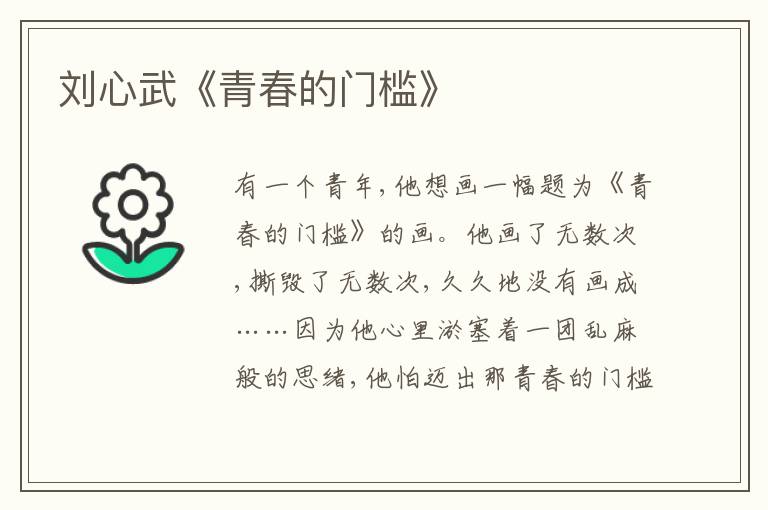我推门出来,满天都是星星,月亮只有半个,像被一把钝刀切开,切口上还留着不太整齐的曲线。它安静地挂在院子的正上方,成了我们家的私有财产。我对母条说,现在才知道,月亮原来是我家院子的肚脐眼儿。母亲笑,忍不住钻进窗帘贴着玻璃往外边瞧。
在这个夜晚,我们家也像是被切成两半儿的月亮。我跟母亲在村庄,弟弟和父亲在医院。
似乎很多年没有跟母亲独处过这么多天。一早,她起床,用左手穿衣服,穿鞋,用左手扶稳一把榆木拐杖,高一步低一步,走出屋子,用脚印把院子丈量两遍,再回来,用左手生火,煮粥。她喜欢提醒我:和面要用温水;别忘了把这盆食端给狗,还有鸡的食也送给它,顺道把鸡蛋也收了吧……她坐在那里指使我干这干那,仿佛二十多年前的光景:她要教会我各种生活的本领,把自己的各种经验倾倒给我,就像月光洒满院子。
她要用那半个身子,释放出对我全部的爱。白天,她怕我在屋子里冷,喊我去晒太阳。太阳看着我们,在椅子底下,刻出一幅母女相依的影子。晚上,她喊我快点去睡。我总是要在睡前为她按摩。她平躺着,身体展现在我面前。她的右胳膊僵硬,右手不由自主地攥起来,右腿明显比左腿短一截。它们都萎缩得厉害。我注意到了她肚脐下边竖着的切口。她注意到了我的目光,解释道,那会儿也是没办法。
那时,她只有二十一岁,怀了我之后,又紧张,又幸福。她感受到我在腹部一天天长大,肚子很快就鼓起来。大家都说她怀的可能是双胞胎。然而,与我一同长大的竟是一个肿瘤。它甚至抢了我的风头,快速地占领着地盘,它让母亲困顿,疲乏,让她瘦弱。几个月后的某天,她终于忍不下去了,坐着父亲赶的牛车进了城里的医院。
大夫望向她和父亲,孩子还要不要?若保孩子,就要等母亲完成分娩后才能手术,那时必定增加风险。若是保大人,现在必须手术,孩子能否成活就听天由命了,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,要保大人。母亲经历了手术,大夫从她腹部取出的肿瘤装了一小盒。之后,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任我自然生长。哪怕我出生后非常健康,她也总是对当时的选择心怀愧疚。我看着这道与我同龄的伤疤,安慰她,如果是我,我也会跟你们做同样地选择。她说,还是有个女儿好。
我查看她的身体,像在观察一棵老树的年轮。除了经历那次手术之外,她还经历过一次绝育术,这是那个时代女人的标配。
她的虎口有一道伤疤,那些年,我们家除了种地,便是喂牛。有一次。她拿着镰刀去割草,在一条细窄的小道上,前边忽然来了一头小牛,她往旁边一躲,不小心掉了一跤,镰刀的刀刃正好割在了虎口上,顿时血流不止。她包着一大块鲜红的布去邻村找大夫,缝了好几针。回来的时候,带回了一块鲜红的布。
她脚上也有一道伤疤。那一年,不知道为什么脚上忽然多出了一块骨头,她去城里看,大夫说那是骨质增生,需要做手术。术后,她坚持没有住院,为了省钱,她坐班车到山下,硬是爬上了山。那天,她坐在堂屋的一把木椅上,用从医院带来的纱布给自己换药。当时,我要赶去两座山那边的村庄上学,一去就是五天。我一走便没有人照顾她,我躲在门后的水缸边哭,她赶我,快走!那些天,她照常喂鸡,喂狗,后来感染了,敷了好久的药才好。
她脖子上也有块比指头肚略小的伤疤。她脑出血之后,昏迷了多日。每天都需要输液,两双手被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后来护士实在无处下手,说要做一个置留管,找来找去,选择在脖子下边的位置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母亲的皮肤上下刀子,那种感觉很不好受,几天之后,母亲忽然双目圆睁,上下牙紧紧咬合,从牙齿的隙缝里分泌出白沫。她犯了癫病。大夫说这可能是脑溢血后遗症。此后又犯过两次,吃了药也无效,我强烈要求护士将它拆除后,母亲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毛病。
躺在炕上,她把心里的伤疤也摊给我看。年少时她受的委屈、她做出的反击,成年之后的无奈,还有现在她的身体。说着说着,她哭了,我伸过手给她抹眼泪,感觉从眼角到发丝里仿佛隐藏着一条隐秘的河流。现在,河水溢出来了。
母亲终于睡着了。窗外的月亮好像不那么明亮了,我隐约看见,它已经斜了过去,去往右边的山梁上方。那里,春天正从一些干枯的枝头上伸出眼睛、耳朵来,虽然暗处仍然有积雪,但有些野草已经开始变绿,有些昆虫已经准备鸣唱,等着打破乡村无风之夜的安宁。多少生命在这样的笋节里待着,期盼着。
我想起生小儿子时,肚子胀得滚圆,生大儿子时留下的那道伤疤几乎要被撑开,成日里心惊胆战。最后的几天,我在灯光下照着镜子,肚皮反着光,我感觉自己像是托着一轮圆月亮,一轮有伤疤的月亮。
深夜里,母亲一次次醒来,给我掖被子。
有一次,我从梦里醒来时,母亲正在熟睡,听着她有节奏的鼻息,忽然觉得她的身体里贮存了满满的月光。有她在的地方,无论多深的夜,我心里都是亮堂的。我忍不住把头偎在她的枕边,仿佛自己还是个婴儿,仿佛她还年轻,仿佛,前边的日子都堆积在阳光里。
我推门出来,满天都是星星,月亮只有半个,像被一把钝刀切开,切口上还留着不太整齐的曲线。它安静地挂在院子的正上方,成了我们家的私有财产。我对母条说,现在才知道,月亮原来是我家院子的肚脐眼儿。母亲笑,忍不住钻进窗帘贴着玻璃往外边瞧。
在这个夜晚,我们家也像是被切成两半儿的月亮。我跟母亲在村庄,弟弟和父亲在医院。
似乎很多年没有跟母亲独处过这么多天。一早,她起床,用左手穿衣服,穿鞋,用左手扶稳一把榆木拐杖,高一步低一步,走出屋子,用脚印把院子丈量两遍,再回来,用左手生火,煮粥。她喜欢提醒我:和面要用温水;别忘了把这盆食端给狗,还有鸡的食也送给它,顺道把鸡蛋也收了吧……她坐在那里指使我干这干那,仿佛二十多年前的光景:她要教会我各种生活的本领,把自己的各种经验倾倒给我,就像月光洒满院子。
她要用那半个身子,释放出对我全部的爱。白天,她怕我在屋子里冷,喊我去晒太阳。太阳看着我们,在椅子底下,刻出一幅母女相依的影子。晚上,她喊我快点去睡。我总是要在睡前为她按摩。她平躺着,身体展现在我面前。她的右胳膊僵硬,右手不由自主地攥起来,右腿明显比左腿短一截。它们都萎缩得厉害。我注意到了她肚脐下边竖着的切口。她注意到了我的目光,解释道,那会儿也是没办法。
那时,她只有二十一岁,怀了我之后,又紧张,又幸福。她感受到我在腹部一天天长大,肚子很快就鼓起来。大家都说她怀的可能是双胞胎。然而,与我一同长大的竟是一个肿瘤。它甚至抢了我的风头,快速地占领着地盘,它让母亲困顿,疲乏,让她瘦弱。几个月后的某天,她终于忍不下去了,坐着父亲赶的牛车进了城里的医院。
大夫望向她和父亲,孩子还要不要?若保孩子,就要等母亲完成分娩后才能手术,那时必定增加风险。若是保大人,现在必须手术,孩子能否成活就听天由命了,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,要保大人。母亲经历了手术,大夫从她腹部取出的肿瘤装了一小盒。之后,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任我自然生长。哪怕我出生后非常健康,她也总是对当时的选择心怀愧疚。我看着这道与我同龄的伤疤,安慰她,如果是我,我也会跟你们做同样地选择。她说,还是有个女儿好。
我查看她的身体,像在观察一棵老树的年轮。除了经历那次手术之外,她还经历过一次绝育术,这是那个时代女人的标配。
她的虎口有一道伤疤,那些年,我们家除了种地,便是喂牛。有一次。她拿着镰刀去割草,在一条细窄的小道上,前边忽然来了一头小牛,她往旁边一躲,不小心掉了一跤,镰刀的刀刃正好割在了虎口上,顿时血流不止。她包着一大块鲜红的布去邻村找大夫,缝了好几针。回来的时候,带回了一块鲜红的布。
她脚上也有一道伤疤。那一年,不知道为什么脚上忽然多出了一块骨头,她去城里看,大夫说那是骨质增生,需要做手术。术后,她坚持没有住院,为了省钱,她坐班车到山下,硬是爬上了山。那天,她坐在堂屋的一把木椅上,用从医院带来的纱布给自己换药。当时,我要赶去两座山那边的村庄上学,一去就是五天。我一走便没有人照顾她,我躲在门后的水缸边哭,她赶我,快走!那些天,她照常喂鸡,喂狗,后来感染了,敷了好久的药才好。
她脖子上也有块比指头肚略小的伤疤。她脑出血之后,昏迷了多日。每天都需要输液,两双手被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后来护士实在无处下手,说要做一个置留管,找来找去,选择在脖子下边的位置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母亲的皮肤上下刀子,那种感觉很不好受,几天之后,母亲忽然双目圆睁,上下牙紧紧咬合,从牙齿的隙缝里分泌出白沫。她犯了癫病。大夫说这可能是脑溢血后遗症。此后又犯过两次,吃了药也无效,我强烈要求护士将它拆除后,母亲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毛病。
躺在炕上,她把心里的伤疤也摊给我看。年少时她受的委屈、她做出的反击,成年之后的无奈,还有现在她的身体。说着说着,她哭了,我伸过手给她抹眼泪,感觉从眼角到发丝里仿佛隐藏着一条隐秘的河流。现在,河水溢出来了。
母亲终于睡着了。窗外的月亮好像不那么明亮了,我隐约看见,它已经斜了过去,去往右边的山梁上方。那里,春天正从一些干枯的枝头上伸出眼睛、耳朵来,虽然暗处仍然有积雪,但有些野草已经开始变绿,有些昆虫已经准备鸣唱,等着打破乡村无风之夜的安宁。多少生命在这样的笋节里待着,期盼着。
我想起生小儿子时,肚子胀得滚圆,生大儿子时留下的那道伤疤几乎要被撑开,成日里心惊胆战。最后的几天,我在灯光下照着镜子,肚皮反着光,我感觉自己像是托着一轮圆月亮,一轮有伤疤的月亮。
深夜里,母亲一次次醒来,给我掖被子。
有一次,我从梦里醒来时,母亲正在熟睡,听着她有节奏的鼻息,忽然觉得她的身体里贮存了满满的月光。有她在的地方,无论多深的夜,我心里都是亮堂的。我忍不住把头偎在她的枕边,仿佛自己还是个婴儿,仿佛她还年轻,仿佛,前边的日子都堆积在阳光里。
上一篇:林清玄《一心一境》
下一篇:刘心武《青春的门槛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