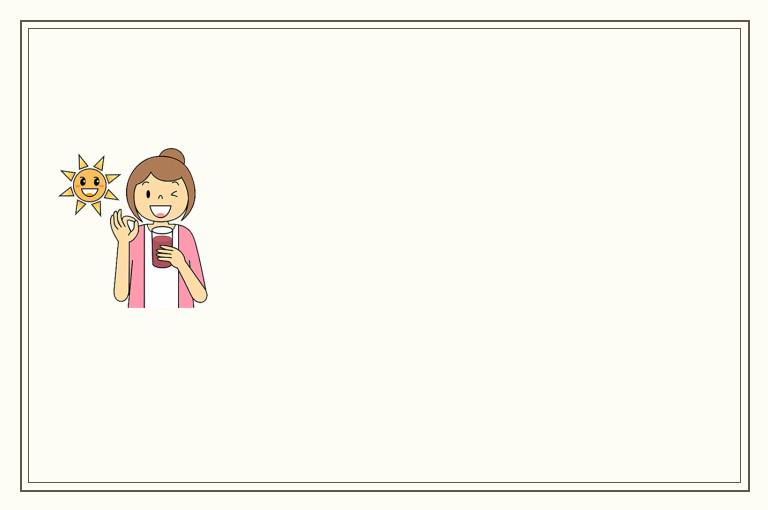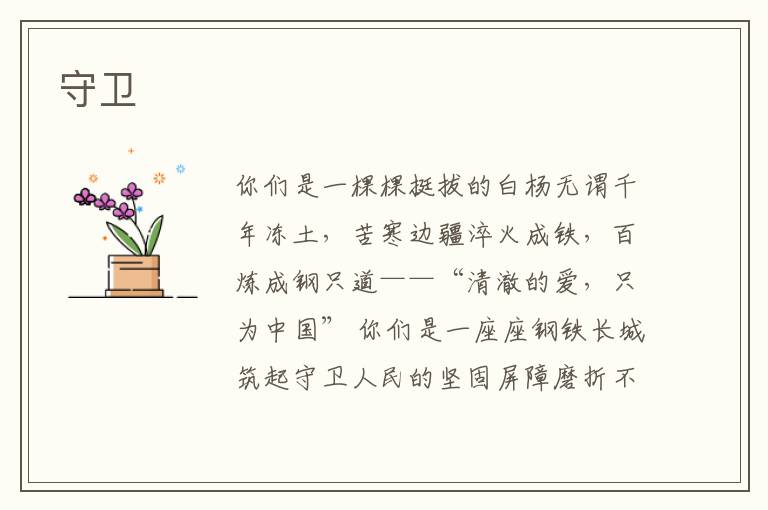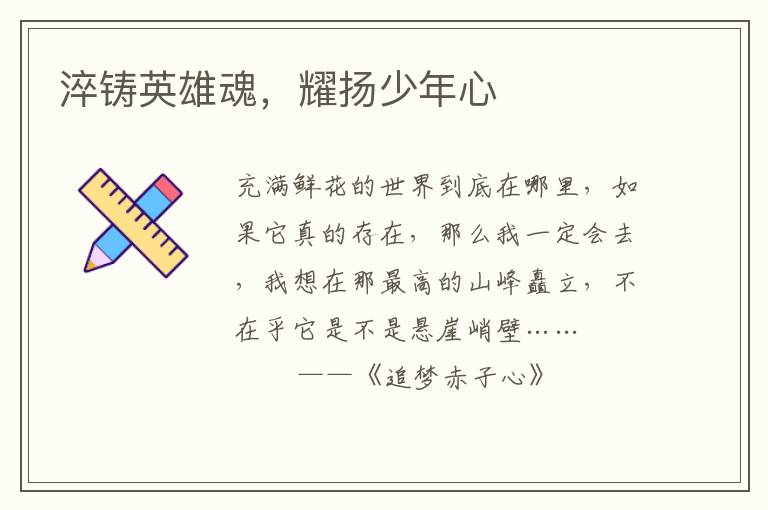路,还是那条老路。即使许久没回,也没有生疏半分,只是颜色变了,从嫩绿变成金黄了……..
我走时是六月份,乡人们早已将稻种播完了,水浸上,太阳一晒,一两个绿头也就钻出来了,陆陆续续的这地就似着魔了般,没一会子功夫就为自己添了件绿衣裳。田中唯一有一条较宽的道,就是这条老路,黄泥巴捞出来的,直,却凸凹不平,这道将整片田一分为二,道尽头那亩较小的地,就是我们的田。
母亲曾告诉我:“看你们多幸福,我们六七岁便上田干活了。”我赤脚走在道上,伸出手便想折下一杆稻谷,母亲急忙打了我的手,我转头抱怨,“那么多呢,拿一根又怎么?“是,你拿一根不怎么,那我拿一根呢,咱全村老少几百号人口都来拿一根呢,这田就活不了。”母亲蹲下来揉我手,严肃的说。我点点头,自那次后,每每想折一根金稻秆拿在手中把玩时,我便打打自己的手。不能让地活不成!

如今,我再次走上这条道,昔日的小女孩怡然成了大人模样,只是对稻谷的这份敬畏从未改变。太阳变成了夕阳,霞光红晕了天地,也红晕了这片田和田中的这条道,我正醉于这幅美景,远处却传来了张伯的呼声,“闺女,这!。”我匆匆跑去,“张伯,这多年不见,您还像原来一样年轻!”“哎哟闺女啊”,你都长这么大了,我这庄稼人整天在这地头风吹日晒的,那还年轻啊,老咯!”他笑起来,黑红的皮肤也皱起来,握着锄头的手上布满了老茧,黄泥似乎渗入了他的手,破旧的上衣被搁在道上,只留那半头白发,随风微微飘动。“张伯,我妈说您儿接您去城里,您却不答应,您毕竟岁数大了,就别跟这田较劲了。多享享福,您儿子牵挂着呢。”我企图劝劝他。“闺女啊,”他擦擦脸上的黄泥,一屁股坐在道上,手里紧杵着锄头说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城里是好,我呢,我五岁就跟家里人下田,这田啊,就是我第二个屋,以前是为了赚钱,养家……”“现在又不缺钱,您还留这干嘛呀!”我急忙应。“是不缺钱,但这田我放不下了,就跟我亲兄弟似的,比亲兄弟都亲呢,你别看这谷肥,说白了,这都是汗灌出来的呀,我大半辈子都给了田,就跟半条命给了它一样,它肥,我乐。它不肥,我愁。都习惯啦,放不下咯!”他又跳下田去,扛起了锄头对我笑:“闺女,我得赶紧搬杆子去了,空了到我家来啊,我给你蒸自己种的米,可香着呢!”我点点头,微笑说,“好,您慢点。”
天色渐沉,我也不再继续走,默默与这一道稻谷作了告别,便转身返家,母亲早在家门口候着我了,看见我,不禁轻怨:“这死丫头,饭都凉了,我再热热去。”我在院子里坐下,与身旁的父亲说起了张伯的事,父亲沉默。风从远处飘来,夹杂着谷的清香混着蝈蝈的私语,越过田,越过道,越过睡熟了的庄稼人,飘向我们又飘过远方。过了一会,父亲开口了:“你知道稻谷怎么种吗?”我被父亲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噎住,看我没应,父亲继续说,“先要整地,后是育苗,再是插秧,在这中间,除草,除虫,施肥,浇灌,排水,那样能落下?熟了后要割谷,晒谷,打谷,筛谷,一样也都少不了。是累,累的不行,但咋们是庄稼人,本该这样,这一粒粒米,那是米啊,是咋们庄稼人的希望啊。”这次是我沉默了。母亲将热好的饭菜端上来,我捧起那一小碗白嫩而肥硕的米饭,一口下去,清香沁人心扉,那碗饭,我一粒都没剩。
夜里,我做了一个梦,梦中有那片田,那条道,道上堆满了金黄的谷子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一个小女孩赤脚趴在在道上,她捧起一把谷子,轻吻一下,殊不知谷子也在亲吻她。
下一篇:不变的爱,只为中国